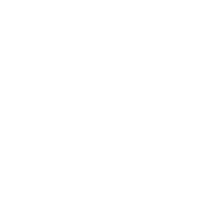在这个被商业大片与视觉奇观统治的圣诞节,一部名为《万王之王》(The King of Kings)的动画电影悄然登陆香港。这部影片并非来自好莱坞的流水线,而是源自英国作家查尔斯·狄更斯尘封百年的私人手稿。穿透维多利亚时代的迷雾与现代都市的喧嚣,我们看见这部动画电影在神学争议、文化博弈与心灵渴望之间,为我们重述那个关于爱与救赎的永恒童话。
一、藏在书桌抽屉里的秘密
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,往往不是在大广场上用喇叭喊出来的。而是在摇曳的烛光下,父亲对着孩子的耳语。
查尔斯·狄更斯,世人皆知他写了《双城记》,写了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他用笔尖挑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脓疮,让整个伦敦为之哭泣。但在1846至1849年间,当处于创作力的巅峰时,他却做了一件“奇怪”的事:他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生平的小书,随即将之束之高阁。
是的,藏了起来。他没有把它交给贪婪的出版商,尽管那能换来成堆的金币。他把书稿锁在抽屉里,定下一条家规:这份手稿只能在每年圣诞节的家庭聚会上,读给他的孩子们听。直到他死后又过了60多年,直到他最后一位在世的儿子亨利·狄更斯于1933年去世,这个秘密才被允许公之于众。
为什么?狄更斯虽然是个天才,但他首先是个父亲。他明白一个现代神学家经常遗忘的常识:信仰首先是一种亲密关系,其次才是一套教义。他不想让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宗教争论,污染了他孩子心中那个仁慈、宽恕、爱护穷人的耶稣形象。
而今,这部电影做了一件聪明、甚至可以说是巧妙的事。它没有直接把《圣经》甩在观众脸上,而是让人们成为“窃听者”。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,是狄更斯(由朱栢康那充满戏剧张力的声音演绎),正试图搞定他那个顽皮的、对信仰毫无兴趣的儿子沃尔特。沃尔特手里挥舞着木剑,满脑子都是亚瑟王的骑士传说,对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毫无敬意。
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。现代文明就像小沃尔特,手里挥舞着科技的木剑,沉迷于漫威英雄和星球大战的虚构神话,却对那个真正改变了历史的“神话”嗤之以鼻。电影《万王之王》不仅是在讲耶稣,更是在讲“如何向一个听不进去的时代讲耶稣”。影片借狄更斯之口说:“让我给你讲一个比亚瑟王更伟大的故事。”这是诱惑——神圣的诱惑。
二、蓝色巨人与马槽里的婴孩
2025年圣诞节的香港街头,金钱与十字架比邻而居。在这个档期里,一场无声的争夺正在打响。
在战场的这一边,是好莱坞的科幻巨兽《阿凡达3》。阿凡达像歌利亚一样巨大,身披数亿美元的特效铠甲,承诺带给观众无与伦比的感官刺激,却也夹杂着未必适合儿童的暴力场面。在战场的另一边,是《万王之王》,一部时长101分钟的动画片,手里只有“爱与宽恕”这几颗光滑的石子。
市场分析师们(一群喜欢用数据解释奇迹的人)称之为“反向排片”策略。他们声称,当《阿凡达》在兜售肾上腺素和IIB级的紧张感时,《万王之王》提供了一个全年龄(I级)的安全港湾。但我更愿意称之为“伯利恒策略”。
2000年前,世界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下喧嚣震天,但在伯利恒的马槽里,只有安静的啼哭。今天,当IMAX屏幕上的蓝色外星人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时,这部电影试图用一种更古老、更温柔的声音说话。
有趣的是,这种“温柔”并非软弱。这部电影背后的制作方Angel Studios,正是那群曾经用《自由之声》震惊了好莱坞的“疯子”。他们不依赖大制片厂的施舍,而是依靠成千上万普通信徒的众筹和投票。这本身就像是一个神迹:在“资本主义”的核心地带,一群人通过“把爱传出去”的模式,不仅在美国拿下了近1900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,更把这部电影推向了全球。
在香港,从坚尼地城的高先电影院,到尖沙咀豪华的MCL K11 Art House,再到英皇戏院在澳门的同步上映,这张放映网撒得既广又深。即便是在最商业化的节日里,人们对“纯真”的饥渴,依然像对面包的饥渴一样真实。
三、乡音中的道成肉身
“道成肉身”,意味着真理穿上当地的衣服,说着当地的方言。如果耶稣只是说着亚兰语,那祂只停留在历史书的插图上;当祂开始说粤语,便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邻舍。
这部电影的配音阵容惊艳。有郑秀文(饰嘉芙莲·狄更斯),香港人都知道她是乐坛“天后”,但也知道她曾跌入抑郁症的深渊,是信仰把她从黑暗中拉了回来。对于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观众来说,她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“安全”的信号:没有审判,只有理解。
这里有王祖蓝(饰彼得)。让他去配那个冲动、偶尔犯傻、却又无比真实的彼得,这个选角简直充满了上帝的幽默感。圣徒从来不是冰冷的大理石雕像,他们是会讲笑话、会跌倒、会像我们一样陷入尴尬的普通人。
还有孙耀威(饰约瑟)和蒋志光(饰希律王)。这些声音,构成了香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。当神圣的故事借由这些熟悉的声音流淌出来时,变成了自家的家常话。它消除了语言的门槛,让那些从未读过《约翰福音》的茶餐厅伙计、的士司机和中环白领,都能听懂那个关于救赎的奥秘。
四、属于孩子的神学:为“不完美”辩护
有些严谨的加尔文主义者或福音派神学家对这部电影皱起了眉头。他们拿着放大镜,指出了影片在神学上的瑕疵:这部电影受狄更斯“唯一神论”(Unitarianism)倾向的影响太深,把耶稣描绘成了一个道德榜样和仁慈的导师,却淡化了祂作为三位一体真神的威严。
他们指出:电影把耶稣的死,解释为为了众人的利益,而不是圣经中严厉的赎价,这稀释了代赎的教义。
他们警告:让小沃尔特在想象中穿越进圣经故事,会混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。
诚然,这些批评在真理和学术上层面都站得住脚。但我们同时也得思考:是培养神学博士必要呢,还是让孩子先爱上耶稣更重要?
狄更斯不是在写《系统神学》,他是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。当一个父亲试图告诉孩子“为什么那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”时,他会讲爱,讲牺牲,讲一个好人为了坏人付出了生命。
这当然不是完美的神学。狄更斯一生都在逃避严酷的教条,甚至他自己也未必完全信服三位一体的奥秘。但上帝似乎并不介意,使用一个神学上的“口吃者”来讲述祂的荣耀。
正如C.S.路易斯所言,有些真理太大了,大到我们只能通过童话的窗户去窥视。狄更斯留下的裂缝,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
电影中的小沃尔特通过想象进入圣经场景。这种被称为“依纳爵式默观”的方法,正是这部电影独特和迷人的地方。我们需要这种神圣的想象力!如果孩子们只能背诵教义问答,却从未在脑海中看见过耶稣在水面上行走,从未感觉过最后晚餐时那沉重的氛围,那么,他们的“信仰”就只能是干瘪的标本。
电影里甚至有一只猫。每当圣经的场面变得过于激烈、太过“血腥”时,镜头会切回狄更斯的客厅,切回那只慵懒的猫,给孩子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这被批评为“打断叙事”,却恰恰让孩子能在“安全的地方”触碰死亡的奥秘。
正如一些明智的机构所建议的,家长应该陪同孩子观看,并在观影后进行引导。这不正是“家庭祭坛”的另一种形式吗?电影不是保姆,它只是工具和途径。这部电影的艺术形式,给了父亲们一个机会,不再把责任完全推给主日学老师,而是像狄更斯一样,亲自对孩子说:“来,如果你觉得电影里有些地方不对,让我们打开那本真正的书看一看。”
五、视觉的巴别塔与灵魂的归乡
最后,我们看看这部电影的“皮囊”。这又是一个全球化的奇迹:一家韩国的特效公司(Mofac Animation),拿着2500万美元的预算(这笔钱对好莱坞而言只是零钱,对独立动画来说是巨款),试图重现一世纪的犹太地。
影片在视觉上,刻意营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质感:狄更斯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伦敦,温暖的、煤气灯下的、像古典油画般的色调;而耶稣所在的犹太地,则是阳光普照的、纹理清晰的、带着纪实感的超写实风格。这种对比似乎在暗示:虽然狄更斯的世界离我们很近,但那个古老的圣经世界才是更真实的现实。
尽管技术上有瑕疵,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见证:来自东方的艺术家(韩国团队),用西方的技术,讲述中东的故事,最后在中国的土地(香港)上引发共鸣。
这不正是“万国都要来就祢的光”的一种当代应验吗?
六、唯一的“真实神话”
2025年的圣诞,站在戏院的排期表前,香港人面临的其实不是两部电影的选择,而是两种渴望的博弈:一种渴望引领飞向潘多拉星球,借助科技的奇观去逃避这个破碎的世界;另一种渴望则邀请我们回到狄更斯的书房,透过摇曳的烛光去拥抱这个世界——因为上帝亲自来到了这里。
不必苛求这部动画在技术上超越好莱坞。它的力量不在于视网膜的震颤,而在于心灵的颤栗。在这个充斥着“后真相”与“虚拟现实”的时代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分辨什么是“被制造的幻觉”,什么是被启示的真理。
狄更斯借着电影告诉我们:“这是一个比亚瑟王更好的故事。”远远不仅这是更好的文学,更因为正如托尔金与C.S.路易斯所顿悟的,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走进现实的神话!
每个人,都需要练习如何去聆听那个古老的、微小的、却足以震碎死亡的声音。
在所有的故事落幕之后,只有这一个,是真的。
注:本文为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。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福音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!